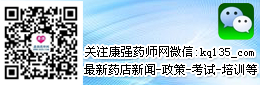从“联”到“合”的步幅
2014-10-17
作者:周玉涛
来源: 中国药店网
访问量:98
次 在线投稿
分别指代联合执法的形式与内容的“联”与“合”实际上也分割了其发展的两个阶段,就目前来看,联合执法正处于自“联”向“合”转归的过渡期。
究其原因:
一则,从制度层面看,各执法主体的执法依据是在“分治”的逻辑下制定的,相对执法场景的转换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联合执法实践中所表现出的“踢皮球”现象固然不能排除主观原因,制度的制约因素更不可忽视。
二则,从执行层面看,联合执法缺乏统筹分工与协作的担纲者,细分领域的专业性决定食品药品主管部门当仁不让,但历史遗留的“小马拉大车”问题却阻断了设计初衷向实际效果的转化。 (1)在新一轮体制改革中,工商、药监、质监三局合一,匹配的是行政职能的重新整合与分配;
(2)公安部于今年3月提出,将在系统内部成立专门指向食品药品的药品侦查局,试图结束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涉刑案件中长期的“代位执法”行为。 2万家药店招聘,6万名药师求职,上康强医疗人才网 www.kq36.com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康强药师网无关。康强药师网站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