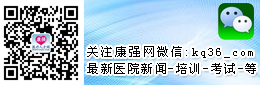两名中国医生接诊几内亚首都****例患者
2014-08-07
来源: 北京晚报
访问量:85
次 在线投稿
埃博拉疫情期间,为了尽可能切断传染链,医疗队的会议改在操场举行。 中国第23批援几内亚医疗队提供 上周,一个从非洲返回香港的女士怀疑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虽然很快被证实是“虚惊一场”,但不禁让人胆战心惊:埃博拉不再是遥远非洲大陆上肆虐的幽灵,它很可能乘坐飞机抵达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半年前,就在国人对埃博拉基本不关注的时候,已经有一群中国人身处埃博拉的漩涡之中,他们就是市卫计委派出的、由安贞医院19名医务人员组成的中国第23批援几内亚医疗队。按计划,他们将于本月底前回国。迄今为止,他们是距离埃博拉最近的中国人。 暴发 援几第二年遭遇埃博拉 北京安贞医院派出的19名医务人员工作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中几友好医院。两年前的夏天,19名医务人员来到这里。在他们的倡议下,中几友好医院设立了像中国医院的交班会,大家一起讨论疑难病例。今年3月17日,是个星期一。中国医疗队队长孔晴宇记得那天早上普外科主任盖斯姆介绍了一个病人。患者是个三四十岁的黑人,两天前急诊住院时出现了发热、恶心、呕吐伴消化道出血等症状。中几友好医院虽然在几内亚是家大医院,实际上科室并不健全。医院里没有消化内科,急诊的值班医生盖达就把患者收到了普外科。很快,患者出现结膜充血和皮肤广泛出血点,但诊断一直不能明确。孔晴宇听完介绍后,感觉有些奇怪,“以前很少见到这样的病例。” 这个病人,医疗队员、普外科医生曹广印象也很深,因为他曾经给患者查过体:他翻开患者的眼睑,发现瞳孔异常,考虑有脑出血,建议CT检查。结果果然有颅内出血。这位患者很快死亡,曹广清楚地记得,患者死亡当天左眼白眼球已完全消失,红得像兔子的眼睛。 埃博拉比非典凶百倍 情况在3月24日发生了变化:几内亚政府发出了手机提醒短信。中几友好医院1周内先后有3名患者因不明原因出血很快死亡,而出血倾向是埃博拉出血热病人终末期的典型症状。这3名患者都是埃博拉吗?很快,队员们的担心变成了现实,3名病人中的第一位病人的4名亲属先后出现发热的症状,同时中几友好医院诊治过此名病人的3名医生、2名护士也相继出现发热。曹广曾经直接给病人进行了查体,医疗队内镜专家吴素萍主任也在工作中接触了其中一名医生。 这样紧张的场景让王薇突然想起了2003年的北京非典,“可这埃博拉出血热要比非典凶残100倍呀!” 隔离 接受隔离很淡定 几内亚是第一次面对埃博拉疫情。它会如何发展?我们该怎么办?面对这个问题,孔晴宇也在思考。孔晴宇是心外科医生,埃博拉病毒对于他来说,同样是陌生的。但这个陌生的病毒很凶险:第一个病人意外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之后,病毒会通过患者的体液进行传播,通过直接接触患者的血液、唾液、尿液、粪便等分泌物,甚至通过飞沫、呕吐物、汗液都可以传播。一旦这些传染物质侵入到人体内,因为没有治疗方法和预防疫苗,没有血清疗法,伴随着的就是很高的感染风险和致死率。 中几友好医院已经有密切接触患者的医务人员死亡了。我们的两名队员应该怎么办?隔离。 隔离,虽然从传染病控制上来说非常必要,但是让老孔把这话说出口,他心里还是很难过。 3月27日下午4点,曹广正在打乒乓球。孔晴宇走了过去,宣布让曹广隔离,他说:“老曹,13亿中国人中你离埃博拉病毒最近了,希望你坚强,你能理解。”曹广二话没说,同意。 中几友好医院的胃镜医生盖达是第一例确诊患者的接诊医生,后来又参加了对该患者的抢救。平时他与医疗队内镜专家吴素萍在一起工作。3月17日上午,吴素萍与盖达一起工作时发现他体力不佳、精神萎靡。很快,盖达出现发热、呕吐等症状,随即被确诊为埃博拉病毒感染。老孔也要宣布让吴素萍隔离,可是吴大夫是位女士,她能承受吗?没想到,吴大夫很淡定地接受了隔离,并且告诉其他队友,“一定会认真做好隔离”。 每天向家报平安 一个人面对未知的风险是非常煎熬的。 曹广平时性情粗放,可是,当埃博拉这个幽灵在他身边徘徊时,他竟然变得细心了。“早上起来洗脸,要在镜子前看自己是不是出现了跟患者相仿的眼结膜出血;白天出现一点点头晕就会开始紧张,想这是不是发病的先兆;试表即便体温刚到36.9摄氏度,也会不自主地心跳加速;就连身上起了一个小疹子,都要联想是不是那个病毒感染造成的。”曹广平时只有渴了才会想起喝水,隔离期间每天强迫自己多喝水;医院给队员们配备的维生素,平时他连看都不看,隔离时却规定自己必须按时吃下以提高身体免疫力;原来喜欢听的评书相声,隔离期间怎么听都感到十分无趣…… 孔晴宇还记得,为了尽量和大家拉开距离而又不间断自己的锻炼,曹广专门选择在人少的下午进行锻炼,顶着骄阳、手持哑铃负重行走。有一天晚上,老孔把一盒号称能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品送给曹广,他当着老孔的面就打开吃了两粒。“我知道埃博拉给他的压力很大。” 老孔说,吴素萍大夫心思缜密,平时特别优雅;不过,还有一个特点:胆小。但是面对埃博拉时,吴大夫特别勇敢。天刚刚亮,别人还在睡觉,她就起床锻炼;天色晚了,别人陆续回宿舍时,她又开始出来健步走。“她把恐惧压在心底,把自信留给大家。” 4月14日,隔离观察结束后,曹广说:“我懂得‘活着’是一件多么幸福而美好的事情……” 追忆 两位“中国通”倒下了 中几友好医院普外科主任盖斯姆在这次疫情中倒下了,他是中几友好医院第一位因感染埃博拉病毒而去世的医务工作者。医疗队员、麻醉医生车昊经常和盖斯姆一起工作。得知这一消息,车昊一下子就蒙了。平时,车昊总是称呼盖斯姆为“盖先生”。盖斯姆曾在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留学近十年并获得博士学位,讲中文时偶尔会蹦出几句地道的武汉话来。车昊说,盖先生******是中几友好医院最负责任的医生。很多次,车昊问他为什么这么玩命地干活,盖先生总是用五个字回答:“为人民服务。”在吴素萍的印象中,盖斯姆非常友好。每次见到吴素萍时,盖斯姆都说:“老师,你好!想家没有?”盖斯姆还曾经在胃镜室用中文给吴素萍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盖斯姆离开后,吴素萍和曹广一起按照中国的风俗,面朝西方为他烧纸,送他一程,愿他一路走好。 这次疫情还夺去了中几友好医院神经内科主任西业卡的生命。孔晴宇说,西业卡曾经在延边学习过,讲的中文带一点北方口音,喜欢喝中国绿茶。西业卡并没有直接接触确诊患者,但参与了被隔离医务人员的救治,主管普外科盖斯姆等人的临床治疗。他在盖斯姆病逝后的****0天突发严重症状,从发病到死亡,仅仅5天,年仅45岁。孔晴宇说,就在西业卡发病前不长时间,他曾经问有没有好的绿茶,能否给他一点尝尝,“我当时说可以呀,但一直没能兑现,真后悔呀!” 手记 19名队员仍坚守在几内亚 去年12月,我曾赴几内亚,专程采访中国医疗队驻地和中几友好医院,回来之后加入了名为“几内亚医疗队”的微信群。平时,这个群不是特别活跃,大家空闲时会发一些笑话、段子,每逢节日也会互相道贺。今年4月初的一天,我发现群里弹出条有点怪的消息,吴素萍主任说“感觉良好,准备锻炼。”这条消息引来了一些人的响应,但我也没有过多关注。4月4日,吴主任又说了一句“两周了,值得庆贺,感觉良好。”紧接着,曹广说“早上体温36.2(摄氏度),请放心。距离接触患者18天,距离接触医生11天。”略懂医学常识的我知道,肯定是出现了传染病。侧面打听后,我知道他们工作的医院出现了埃博拉出血热患者,并且患者已经死亡,还有当地的医务人员被传染后死亡,其中包括我们在非洲期间曾经见过的普外科医生盖斯姆。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埃博拉离我很近,有“细思恐极”之后的庆幸,甚至在想:是不是要感谢命运的眷顾,我在非洲的时候没赶上埃博拉,没遇到疟疾、霍乱、黄热病…… 这之后,我注意到,吴素萍和曹广每天都在微信群里数日子,在群里报体温。4月13日,曹广在群里说,“最危险的华人已经基本安全,全中国都安全了。呵呵呵!目前应该没有华人发病。”他们解除隔离后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14日,正赶上安贞医院的30岁的生日。安贞医院拍了一张有心脏图案装点的全家福大照片,医疗队员们被放在了心尖上。 如今,这19名医疗队员仍然坚守在大西洋边。 大西洋的海风吹不走埃博拉病毒,但可以带去我们的祝福。希望他们都健康归来。 12万家医院招聘,60万名医生护士求职,上康强医疗人才网 www.kq36.com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康强药师网无关。康强药师网站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