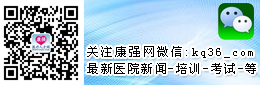乡医渐老“后生”谁来接棒
2012-09-28
来源: 肇庆都市报道
访问量:209
次 在线投稿
当64岁的梁秀群一瘸一拐地穿过睦岗大龙村的小巷去探访病人时,卫生站后继无人的忧虑时常浮上心头。而75岁的邹柱强则显得乐观轻松,他经营了50多年的蕉园外坑卫生站,现在基本交给儿子,他乐得清闲。在我市,像上述的村卫生站有2000多个。从几年前的“赤脚医生”转身成乡村卫生站,从完全的自收自支到每年有政府补贴,这自然让人高兴。但是因乡村落后,全市村卫生站几乎看不见年轻人的身影。人才缺失,已经成为制约村卫生站生存、发展的瓶颈,如何吸引年轻医生下乡驻村,这是一个亟需破解的难题。
邹柱强在自家药房研磨中药。 走访老乡医的呼唤——“我老了,谁来接班” 20日下午,记者在位于端州区最偏远的睦岗大龙村卫生站见到梁秀群时,她正和几位村民闲聊。几位村民都说,“梁医生很好的,跟我们都很熟”。其中一位介绍,“家婆、我、儿媳生孩子,都是梁秀群接生的”。 梁秀群负责大龙村13个村小组的卫生保健工作,每天上午在卫生站坐诊,下午就下乡探访,最远的地方要走近40分钟。她站起来背药箱准备出门时,记者发现她一瘸一拐的。“2002年的一天中午,我开摩托车去看病人,跟另一辆摩托车相撞,医好后就变成这样了。”她笑笑说。去年,她领到了残疾证。 梁秀群现在64岁,20岁左右开始在村里做医生,以前是“赤脚医生”,是村里选出来的,给村民看病就是挣工分。 家人几次劝梁秀群退休安享晚年,尤其是车祸之后。她原本打算将村卫生站交给二儿媳打理,但是“她不肯,去了制衣厂打工,每个月有两千多元”,而在村卫生站,除了那每年一万元的政府补贴,“赚的钱没有打工多”。之前卫生站也来过两个中专毕业的年轻人,但因觉得没有前途或钱途,不久便走了。 “趁现在身体还行,继续做着吧。如果我不做了,真的不知道该交给谁。”梁秀群显得十分忧虑。 四十多个同行,只有几个坚守 在321国道边的蕉园外坑村卫生站,75岁的邹柱强精神矍铄,基本上所有工作都交给了儿子,一般他只看远道而来的病人,“行医50多年了,经常有病人从外地找过来,虽说现在已退休,但不看对不起他们”。 1966年6月22日,是改变邹柱强人生轨迹的一个日子。“那天,*********主席说要将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他记忆深刻,那天之后,原本学兽医的他,被贫下中农选中,参加培训,当起村里的医生,那时他才年仅19岁,“什么都看,感冒发烧、儿科妇科等等,空闲时间还要上山采药。” “做村医,就要24小时待命,现在情况好点,看的多是外地人,多是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如今,他们家三代学医,“儿子从卫校毕业后,一直跟着我边学习边实践,现在我会的他都会,交棒给他我也很放心。大孙子在新兴读书,也是学医的。” 邹柱强感慨说:“这么多年,当时同个班培训的40多人,现在只有五六个还在做乡医,其他的都转行了,我从来没想过转行,这或许就是上天的安排吧。” 年轻乡医的心声——收入不高,不想做乡医 2003年中专毕业后,学医的陆少阳到顺德等地找工作无果,才无奈地回到高要协助在村里当乡医的父亲。大概四年后,他到隔壁村当起了乡医,但不到一年,就不做了。“太辛苦了,吃饭、睡觉都不固定,每个月最高收入也就一千七八,现在随便找份工作,都有这个工资了。” 他介绍,班里的同学毕业后基本上都转行了。这几年,他一直在坚持进修,目前在一家民营诊所坐诊。说到乡医后继无人问题,他有点无奈:“年轻人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乡村真的不太适合,只能另谋出路。”当记者问到,若他的父亲有一天没能力继续做乡医了,他会不会回去接班时,他只是说“看情况吧,当然是希望不回去。” 转变 乡医职能转为负责保健为主 据了解,我市以行政村为单位设置村卫生站,全市卫生站总数超过2000个,每个卫生站都由一名乡村医生撑起,部分行政村人口较多,也会增设一两个卫生站。 如今的乡村卫生站包括乡村医生,承担得更多的是公共卫生服务中的保健作用,遇到重病、大病等,一般都会转送到镇级、县级卫生院。 在梁秀群的卫生站里,门口悬挂着坐诊、下乡的时间表,墙壁则挂着大龙村村民的基本情况和卫生信息,包括各年龄段人口多少、孕产妇人数和儿童预防接种的统计等等。 “有个村民,去年在地里干活,因为高血压突然晕倒,两个多小时后才被发现,我立即联系睦岗医院,将他送去救治。若是在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可能就是我一个人在抢救。”梁秀群介绍说,她现在主要做的工作,就是到各村探访瘫痪在床、行动不便的老人或者旧病患,并记录他们的情况。“村里有人去世了,也要到我这里来登记。” 市卫生局医政科科长江少华介绍,乡医从以前的“赤脚医生”“转正”后,因他们水平、资源有限,承担得更多的是帮村民建立健康档案之类的工作,看病可以说已经不是主要内容,“当然,那些距离镇里十几里远交通不便的山村,乡医还是非常重要的。” 困局 多数村卫生站面临后继无人 按照医改的政策,将病人引入基层、留在基层是一个较为重要的政策,然而,如何让病人愿意在基层看病,即使现在实施了医生挂村服务,即在县、镇派出医生与各个村小组挂钩看病,但是“人才没有,医疗水平不高”,大家还是喜欢挤到大医院看病。 江少华介绍,即使是实施的挂点帮扶服务,也只是到镇一级,没有延伸到村卫生站。现在的模式是在前几年建立起来的,也就是将村卫生站的管理交给当地镇卫生院,但不牵涉到人事。 “多数村卫生站延续的方式是,由乡医的儿子等亲戚接班,没人愿意接班又招聘不到的话,就由当地卫生局开班培训”。在这方面,已经有例子出现,在怀集,有些偏远的山村村卫生站后继无人,怀集卫生局就在当地开设农村医疗培训班,符合条件的就可以承担乡医一职。 “老实说,他们确实比较难维持,如今实行基础药价,看个病,总共才10元、20元,每年一万元的补贴是按照行政村给的,如果一个村有两三个卫生站,那就平均分。”而到工厂打工,每个月一般有2000元左右,“这是人才流失最主要的原因。” 思考 过半乡医近70岁 镇村一体化能否破局 医改政策中,镇村一体化是一个重要的内容,也就是,将村卫生站完全纳入镇级卫生院,包括人员编制,但肇庆目前的医改暂未涉及。“这受限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江少华认为。 有想法、有决心很重要,但资金在哪里?据了解,现在的村医,无社保和养老金,“手停口停”,如果将他们全部纳入镇卫生院的编制,他们当然愿意,关键在于,购买社保、养老、发工资的钱,谁来出? “全市2000多个乡医,这是一笔很大的费用”,整编还将面临更多的问题,“即使有编制,有工资,但是农村条件差,谁愿意去驻站?年轻乡医基本是没有的。” 种种原因导致了如今肇庆乡医都是中老年人,老年人占了过半数。“没有明文规定达到退休年龄不能担任乡医工作,但是一般是超过了65岁,就不建议继续担任了。”而事实上,在去年市三院在高要举办的蛇伤救治培训班上,记者了解到,过半乡医接近70岁,特别是在高要活道等偏远山村。 “农村医疗一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才,现在能做的是,在当地培训或者由卫生部门招聘。镇村一体化,老实说,还有点遥远。”江少华说。
12万家医院招聘,60万名医生护士求职,上康强医疗人才网 www.kq36.com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康强药师网无关。康强药师网站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