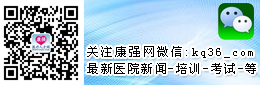博爱医院“破产”调查 院长掏空医院另做投资
2012-09-24
来源: 都市时报
访问量:291
次 在线投稿
博爱医院的物品、资产被搬走卖掉,屋里空空如也
很多人在跟“白大褂”讨价还价
医院里的桌、椅等物品都被变卖
云南博爱医院前途未卜 刀刚失业了。他供职了近10年的单位——云南博爱医院,因管理混乱、缺乏资金,突然死掉了。 这是一家有着22年历史的民营医院,挂靠在云南省康复医学会名下,也是全国为数不多还存在的社会团体名下的集体企业。 员工们觉得,除了管理和资金因素之外,医院的死掉跟时任院长刘夏村有很大关系。集体医院存在的制度漏洞,使得院长权力无法制约;而医院的改制博弈最终失败。员工们指责称,虽然众叛亲离,刘夏村依然可以掏空医院,肥己后另做投资。而投资又是其他投资人干涉不得的独断方式,因而被称为“医院倒了院长却发了”。 只是,面对各种指控,院长刘夏村保持沉默。 贱卖医疗器械 医院的院子里堆满了医疗器械和办公桌椅。很多人在跟穿白大褂的同事讨价还价,感觉就像进了一个大卖场。 9月1日,刀刚来到位于麻园村的云南博爱医院。这是他最后一天来这里上班了。在医院的院子里,病床、床头柜,还有护士办公前台等医院用品杂乱无章地摆放着。刀刚说,他一进门,感觉就像进了一个大卖场。“院子里堆满了医疗器械和办公桌椅,很多人在跟穿白大褂的同事讨价还价。” 看着这些,尽管刀刚心里不是滋味,但他还是走上前去帮忙吆喝。“便宜了、便宜了,所有东西大甩卖。”没一会儿,一帮人围了过来。一张七成新的办公桌,几十块钱就卖了。 其实早在3天前,医院就已经清走了所有的病人,41名留守的职工开始把东西搬到院子里。看着那些自己用了很多年的东西被人买走,刀刚心里很愤怒,他恨不得把那些东西摔个粉碎。“用久了,是会有感情的。” 5个月前,刀刚怎么也不会想到,云南博爱医院会落得如此下场。尽管那时候医院已面临着搬迁问题——10年前,云南博爱医院租下这栋5层的楼房作为办公地点,租期到今年的6月30日止。 今年4月,副院长郭新义考虑到合约到期后,医院要迁往新的地点,就同时任院长刘夏村商量,如何处理医院的搬离问题。 郭新义回忆,刘夏村劝他“不要急,问题总会有解决的办法”。郭新义不放心,还是和刀刚等医院职工分头在昆明市区找房子。但几个月下来,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不是地方太小,就是租金太贵。” 此时,医院的职工也没太着急,他们觉得院长刘夏村会有办法的。然而他们却没想到,在租约到期后,刘夏村却再也不理此事。打电话不接,还以她“已到退休年龄”为由,向云南省康复医学会提交了辞职报告。“她退休了,医院也倒了。”郭新义说。 房东见郭新义等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便答应给他们延长2个月的租期。 郭新义等人不想让云南博爱医院就此死掉,便开始跟房东商谈是否能续租楼房。但一算下来,郭新义发现,医院付房租的钱都不够了。“只有几十万,怎么租?如果按照以前的年租金付,还勉强过得去,但现在一涨,怎么也付不起。” 无奈,郭新义只得向云南省康复医学会打了一个要贱卖医疗器械的报告,云南省康复医学会最终同意了。“医院租用的场地到期了,必须搬走,医院没有资金和场地安置这些用品。另外,医院现在濒临破产,需要资金安置员工。” “医院里的桌、椅、床、电脑和部分医疗器械,我们都卖。头几天卖的是比较贵重的医疗器械,药品和注射器等医疗用品,要么退给厂家,要么送到医疗垃圾处理站。最后一天就只剩一些家具了。”郭新义说,该卖的东西都差不多卖完了,共进账30多万元。这些钱主要用来安置职工。 从普工到副院长 1997年,刘夏村进入博爱医院上班。当时她只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2000年,第一任院长退休后几个月,刘夏村升任博爱医院副院长。 云南博爱医院的前身为云南省康复中心,1990年6月成立。本报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云南省康复中心成立之初,资金主要来源于个人和单位集资。它是隶属云南省康复医学会的康复医疗实体企业,为集体所有制。 参与了云南博爱医院建设的王荣,如今是该院的护士长。尽管时间已过20多年,但她依然清晰记得康复中心建立之初的情况。 王荣说,那时因为资金不足,就在人民西路赵家堆租了一幢5层小楼,作为医院临时的办公地点。“那时整个医院也就20个人,我是刚从学校毕业就去那里上班。因为这是云南省第一家康复医院,大家都觉得挺有发展前景,个人前途也好。” 医院的启动资金为17万余元。其中有1.06万元来自康复医学会,工作人员集资7.2万元,其余来自别的单位出资。 康复中心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还清了当初成立时所有单位和个人出资的钱。王荣记得,那时康复中心的生意特别好,一年四季都没有空床,有时候还得托关系才能找到床位。“医院走廊上住的都是病人。” 不久,康复中心改名云南博爱医院。此时,医院已有医生、护士50多人。 1997年,郭新义进入博爱医院临床科,几个月后,刘夏村也进入博爱医院上班。知情者透露,当时的刘夏村是 云南省康复医学会设在博爱医院办公室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平时工作就是“送送资料、扫扫地、打打开水”。 郭新义第一次见到刘夏村时,他觉得这个人很好、很谦虚,说问题时都是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然而,他说他没想到这个人日后会给医院带来巨大改变。 郭新义和刘夏村进入博爱医院时,正好赶上医院扩张之年。那一年,第一任院长王丽英(已故)为了医院能有个更好的环境,经职工大会同意,在经开区金牛路买了15亩地,准备来日盖医院办公大楼用。后来,考虑到医院资金紧张,又退掉了5亩地。同年,博爱医院办公大楼开始建设。“那段时间大家都很兴奋,天天盼着搬进新办公楼,也算是有个家了。”王荣说。 2年后,云南博爱医院正式搬进新建的5层大楼。新大楼有了,但博爱医院却欠下了外包工程款近100万元。王荣回忆,那时候工程队的人经常上门要钱,还动不动就把医院大门封掉,不让病人进去。 为了还清欠款,让医院早日恢复正常秩序,王丽英提出了两个意见。“一个是卖掉大楼还工程款,剩余的钱用来再建新楼;一个是到外面找合作,引资金到医院来。”医院维修工李家路说,当时开职工大会时,每个人都填了这样一份征求意见的表格。 李家路说,当时大多数职工都选择了后一项。“只要医院在,我们就有希望。要是医院没了,不确定的因素就太多了。” 然而,就在结果还没有定论之时,王丽英退休了。云南省康复医学会指派时任学会秘书长敖丽娟接任院长一职。几个月后,刘夏村升任博爱医院副院长。 更让郭新义想不到的是,没多久,刘夏村代替敖丽娟,出任了院长一职。“敖丽娟在召开职工大会时,说她没有时间来管理医院,虽然她是院长,但她有她的工作,以后医院的主要工作都由刘夏村负责。”郭新义说,“敖丽娟说她只是一个过渡,以后院长就由刘夏村做。” 传统上,院长一职都是由康复医学会指定,因此职工们并没有太多反对。但是,在以后的接触中,郭新义发现,刘夏村是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性格的人。 记者打电话向刘夏村求证,但她拒绝了本报记者的所有采访请求。敖丽娟也同样拒绝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未完成的改制 在一次会议上,郭新义提出要建立财务公开制度,这让刘夏村非常不悦,她拿起账本摔在了桌子上。类似的改制2003年时就曾被提起,但并未实施。 刘夏村接任博爱医院院长一年后,以580万元的价格把医院大楼卖给了原地矿技术学院(现国土资源学院)。 在还掉欠的工程款后,剩余的钱并没有拿来建新房。医院只是在麻园村租了一栋房子。“经过10年的努力,我们医院又回到了原点。”王荣说。 2002年7月,博爱医院正式搬到麻园村一栋5层的楼房里。王荣清晰地记得,搬医院时去了十多辆货车,她就坐在第一排的货车上带路。“很悲惨,眼泪差一点都下来了。如果当时是引资进医院合作,现在那栋大楼得值多少钱啊。”王荣说,那个决定,让博爱医院失去了一次很好的发展机会。 对刘夏村不满的人透露,刘夏村接任院长后,开始安插自己的亲人进医院上班。在搬到新址后,刘夏村的弟弟刘军文进入博爱医院。“表面上他是来开车的,但实际上就是后勤处长。除了采购物资的事情他亲自干以外,别的什么都不干。”李家路说。 2003年,刘夏村找到当时还在药房上班的王荣,说是有个朋友要来药房实习,让她“照顾一下”。事后,王荣才知道,这个“朋友”就是刘夏村的妹妹刘玉倩。王荣说,刘玉倩在药房待了3个月,根本不懂抓药,完全胜任不了工作。 而据本报记者调查,刘玉倩不是学医出身,在进入博爱医院上班之前,她是云南云锡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工。 就在此时,博爱医院申请了云南定点医保医院。刘玉倩便去了医保科,做了系统管理员。“后来她就自然成了医院医保办主任。”王荣说。 也是在同一年,刘夏村的另一个弟弟刘金辉进入医院康复科工作。然而,刘金辉仅仅只待了20多天,就主动辞职离开医院。“他跟我聊天时说,拿着工资,做不了事,心里有愧。”李家路说。 记者调查得知,刘金辉在进入博爱医院前,是一名裁缝。“他父母是做裁缝的,不想手艺失传,就把他留在家里学做衣服。”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说。 但是,离开还不到一年,刘金辉再次进入博爱医院。“那时候食堂刚刚做起来,他就过来做了食堂的管理员,工资拿得比我还高。”李家路说,他那时每个月工资只有980元,而刘金辉的月薪是1040元。 近日,网上传出一份署名为“云南博爱医院职工”的帖子,称:“刘夏村利用一权独大的便利,伙同妹妹刘玉倩、弟弟刘军文长期从医院外购物资、医院基础建设中索贿,并用各类票据冠以手续费、接待费从财务套取现金,经医院小组粗查,涉案金额至少有60万元。医院上下尽人皆知,因为身微言轻,敢怒而不敢言。” 由于刘夏村拒绝了采访,因此无法向她本人核实这种说法的真伪。 但是,医院管理的混乱让郭新义和刀刚等人觉得,是时候让医院的财务公开账目了。“医院一年支出了多少钱、一年赚了多少钱,除了她(刘夏村)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郭新义说。 在一次会议上,郭新义提出要建立财务公开制度,这让刘夏村非常不悦,“拿起一个账本就摔在桌子上。”郭新义说,此后,就再也没有人重提财务制度改革。 改制在2003年曾被提起,但并未实施。“不仅没有推进改制,而且还存在私自占有集体财产行为。”敖丽娟说,博爱医院的破产既不是投资失败,更不是改制失败,而是医院内部人员“损公肥私”,并且拉帮结派“窝里斗”。 这次没有实施的改制,让博爱医院再次错过了走上正轨的机会。“还是没有限制住一些人的权力。”郭新义说。 医院何去何从? 一份会议纪要显示,刘夏村持有医院40%的股权转让价格为480万元。郭新义等人觉得,这笔钱本应该属于博爱医院,如今却是“肥了个人,坑死了医院”。 2008年,考虑到博爱医院在麻园村的楼房租约只有4年且就要到期。刘夏村提议,由博爱医院出资,投资一家新的医院,命名为怡园康复医院,并最终通过职工大会同意。“大家的考虑是,以后博爱医院楼房到期后,租不到房子,就都搬去怡园康复医院办公。”郭新义说。 2009年5月7日,怡园康复医院正式开业。“博爱医院为此投资了280万余元,包括设备、人才等,都是由博爱医院拉过去的。”郭新义说,“投资了怡园康复医院后,就基本上把博爱医院掏空了。” 然而,因为不够500万元资金,导致怡园康复医院不能在省民政厅注册。刘夏村便通过朋友找到云南业邦投资有限公司老板伍氏荣,希望跟他一起合伙,投资怡园康复医院。 伍氏荣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怕刘夏村等人骗他,所以要求他们一起共同出资。最后,500万元资金由伍氏荣和公司共拿360万元,其余的140万元则由当时的博爱医院高层和中层共同凑齐。据本报记者调查,当时博爱医院高层有8人为新投资的怡园康复医院的股东,其中包括郭新义、刘夏村的弟弟刘军文,以及当时博爱医院的财务主管堂建。但在那份股东章程上,并未出现刘夏村的名字。 不过,郭新义告诉记者,刘夏村是隐身的股东,“作为一个法人,如果不拿好处,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 然而,伍氏荣入资仅仅一年后,怡园康复医院就面临拆迁。这让伍氏荣很是愤怒,也让他失去了继续投资的信心。随着伍氏荣撤资,其余的由博爱医院持股的8名股东也纷纷抽身。此后,怡园康复医院由孙小艳和另外一个名叫刘春娥的人合伙接手。刘夏村仍兼任医院院长一职。 此时,刘夏村占有怡园康复医院40%的股份,其中10%为干股。孙小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她接手医院后,刘夏村也想出资占30%的股份,“我怕她没有钱,但她一直告诉我说有钱。” 孙小艳同意之后,她的担心也变成现实。孙小艳说,刘夏村仅仅只拿了53万元出来,这其中,有50万元还是她借给刘夏村的。“剩下的110万,她就说先欠着医院,以后慢慢还。” 但在合作了一段时间后,刘夏村的做事方式彻底让她愤怒了。“投资不是这样玩的,做人也不是这样做的。”孙小艳说,“报账的发票不管是真是假,都拿过来报,想用多少就用多少。” 同样是来自网上的一个帖子称:“刘夏村担任云南博爱医院院长期间,还与老板孙小艳合伙开办云南怡园康复医院,持有40%股份的同时还兼任院长一职,故伎重施,长期从医院外购物资、医院基础建设中索贿,并用各类票据冠以手续费、接待费,从财务套取现金,涉案金额高达120万元。” 但此事并未得到孙小艳的证实。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该吃的亏都吃了,亏的钱也亏了,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想再谈,也不想再跟她扯了。” 孙小艳让刘夏村公开财务状况,却招来了刘夏村的不满。“她说我没有这个权力。”孙小艳说,“我觉得这样的人再也不能继续合作下去了。” 2012年5月27日,孙小艳、刘夏村、刘春娥股东三人在怡园康复医院会议室讨论了医院未来的发展问题。三人一致同意,2012年6月3日前,优先由刘夏村筹集资金,受让孙小艳和刘春娥合计持有的医院60%的股份;2012年6月3日前,若刘夏村放弃优先权或未能筹集足够股权受让资金,则由孙小艳和刘春娥筹集资金受让刘夏村持有的40%的股份。 最终,在7月31日前,刘夏村退出怡园康复医院。至于具体拿到了多少钱,孙小艳不愿透露。但本报记者获得的她们当天开会的一份会议纪要显示,刘夏村持有医院40%的股权转让价格为480万元。 郭新义等人觉得,这笔钱本应该属于云南博爱医院,可如今,却是“肥了私人,死了公家”。 郭新义说,他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带着留守医院的职工向刘夏村维权,讨回本来应归医院的资金。对于博爱医院的未来,他和留守的职工还在等待新资金的注入。“到那时,医院就可以重新开业了。” 12万家医院招聘,60万名医生护士求职,上康强医疗人才网 www.kq36.com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康强药师网无关。康强药师网站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