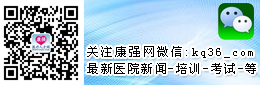人何为什么会接吻
2012-09-21
来源: 大公网
访问量:386
次 在线投稿
青春期 其他动物没有青春期。就连我们的近亲猿类也从幼年到成年过渡得那么顺利。为什么我们人类却要经历近10年的苦恼或者烦躁?青春期一直被看作是一种生殖准备,但现在,通过对人类青春期的深入理解,科学家给出了一些更有趣的解释。 《青春期:一部自然史》一书的作者、剑桥大学的大卫·班布里基称,关于青春期存在两大线索。第一是青春期的进化何时开始。来自前人类化石的骨骼和牙齿发育的证据显示,青春期的进化出现在80万年到30万年前的某个时候。他指出,它先于人脑面积的大飞跃时期,在这一飞跃时期,我们祖先的大脑经历最后一次大扩张,达到今天的大小。第二个线索来自神经生物学和脑成像,科学家们发现,在青春期人类大脑进行了大规模的再组织。班布里基说:“人20岁时大脑的大小和12岁时基本一致,但是,我们仍需要对它进行大量研究探索。” 班布里基认为,青春期不只是为了实现性成熟,它更重要的是为了发展协调心理和社会方面的心智能力,这使得人的生活有别于其他动物。他说:“不经历青春期,我们不会成为真正的人。它们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英国人类学家、拉夫堡大学巴里·伯吉对青春期的理解与班布里基略有不同。他的解释来自对青春期女孩和男孩的观察结果,这些孩子经历着自己成长和发展的特征模式,对女孩来说,青春发育突增期发生较早,因此她们在生殖完全成熟前的数年就表现出了性成熟。伯吉说:“她们进入了成年女性的网络。”这让女孩不仅锻炼了她们日后所需要的技能,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建立了各种联系。他指出,人类进化形成一种合作哺育模式,在该模式中,成功取决于两个家庭和非家庭成员之间共同抚养儿童。 相比之下,男孩的性成熟发生在他们的雄性体格形成之前很久。伯吉争辩说,这让少年们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中学习吸引潜在配偶的优选品质,如语言创造力、幽默和艺术才能,因为他们的稚气未脱意味着成熟的男人不把他们当做威胁。伯吉说:“我认为青春期是一个调和期。”在这10年投入时间学习更重要的认知、实践和物质资源,男孩和女孩可提高他们日后成功再生产的机会。他说:“这就是所有附加价值。”
做梦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如是说:“解释梦境是了解心理潜意识活动的一个捷径。”然而,目前大部分研究人员拒绝接受他认为做梦是我们潜意识欲望的表现的观点,不过为什么人类会做梦的问题,对研究人员的吸引力比以往更大。 做梦并非毫无意义,它们也确实并非没有一点用处。首先,它们对情感处理至关重要。波士顿大学的帕特里克·麦克纳马拉(Patrick McNamara)说:“做梦有助于调节情绪,它们使情绪保持在一定范围内。”最新研究发现,小睡有助于巩固情绪记忆,睡觉过程中快速眼动(REM)的时间越多,对这些方面的记忆就越有利。 一种观点认为,快速眼动梦境使我们重新体验有效的情绪记忆,但是并没有伴随真实体验的大量应激激素涌出。我们通过这种方式保持记忆,但是与之相关的情绪会逐渐得到缓解。快速眼动梦境还有助于其他类型的记忆,并有助于解决一些难题。例如,与白天保持相同时间的清醒后相比,睡一夜后我们能更好地回想起相关单词,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 最近发现,并非所有梦境都发生在快速眼动睡眠时期,这暗示非快速眼动时间段做梦自有其独特功能。麦克纳马拉和同事们分别在学生们快速眼动和非快速眼动睡眠时期把他们叫醒,结果发现快速眼动时期做的梦更像故事,里面参杂了更多情感内容,更加具有攻击性,而且比非快速眼动时期做的梦里面不认识的人物更多,非快速眼动梦境通常包括友好的社会互动。麦克纳马拉认为,快速眼动梦境通过模拟具有攻击性的遭遇,帮助我们应对类似的真实遭遇。而非快速眼动梦境则有助于友好合作行为。 梦境涉及的内容会受到气味甚至地球磁场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但是有些梦境会一再出现。很多快速眼动梦境里有不认识的男性,他通常与做梦的人存在攻击性社会互动行为。发现梦境的普遍主题,预示着梦境意义研究的重新兴起,这次的研究依据是科学。麦克纳马拉说:“这说明最终我们可能会给不同梦境得出相应解释。”
利他主义 如果你认为世上不存在像利他主义这样的事情,那么说明你并不孤独,具有团队意识。在《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写道,“我们必须尝试让人学会宽容和利他主义,因为人一生下来就是自私的。”纵然我们都善待家人,而且不求回报,这是因为至少从生物学角度讲,我们会从这种关系获益:他们与我们的部分基因相同,所以,通过帮助家人,我们可以间接提升自身基因质量。 与此同时,其他看似利他主义的行为常常是互惠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给我挠痒痒,我也会给你挠——不管有多迟——这同样不是某一方的无私付出。这对于利于人类生存的进化意义重大,因为不求回报地投入金钱和精力去帮助别人,会让你在生存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的问题是,近年来的证据表明,人们确实会从事真正的利他行为。 例如,在玩游戏时,许多人会与陌生人“分钱”,即便对方可能并没有直接让其赢到钱。生物学家由此总结得出,利他主义是人类的天性使然。不过,他们仍不能确定利他主义的进化过程及原因。美国新泽西罗特格斯大学的罗伯特·特里沃斯(Robert Trivers)介绍,纯粹的利他主义是一种误读。 他认为,自然选择之所以倾向于那些无私奉献的人,是因为在我们祖先所生活的人数不多、关系紧密的族群内部,利他主义者可能认为“好心会有好报”。但是,在当今全球化的环境下,我们的许多交往是与我们不认识的人完成的,或许跟他们永远不会再相见,所以,我们的无私倾向非明智之举:他们的付出可能得不到回报,由此不适应这个环境。 有些人不赞同这一说法。他们认为利他主义并非遗传进化的产物。他们强调,自我们的祖先开始通过文化塑造环境以来,我们已通过基因与文化的协同进化过程得到发展。正如协同进化偏爱那些对个人有益的特征,这同样会选择使一部分人而非另一部分人受益的特征——利他主义就是这样演变而来。 利他主义对社会凝聚力至关重要。那些凝聚力更强的族群比其他族群更有可能在相互交往中生存下来。从机械学层面来看,基因-文化协同进化言之有理。世上存在增强利他主义的社会机制:例如,担心惩罚,树立信誉,公平理念,宗教或权威人物的谆谆教诲。另外还有种种迹象表明,利他主义还具有生物学根源。 大脑成像技术表明,它可以刺激人脑中给予奖励的区域。此外,具有一种名为AVPR1特定基因的人比没有这种基因的人更无私。他们的大脑更易受后叶加压素(vasopressin)的影响,这是一种在社会依恋(包括母爱和情爱)中起重要作用的激素。当然,有些人或许认为,如果任意友善的行为都能让我们的精神感到愉悦,那么这就不是纯粹的利他行为。
艺术 在漫长的进化之旅中,生存显然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在此过程中,人类却也热衷于创作艺术作品,这不免让人感到有些奇怪。由于这种怪异性,我们在解释人类为何热衷艺术创作时不免面临一定挑战。达尔文认为艺术的起源在于性选择。阿尔伯克基新墨西哥州大学的杰弗里·米勒对此持赞同态度。他指出,艺术就像是孔雀的尾巴,是人类适应性进化过程中一个昂贵的展品。 米勒的研究显示,人类的一般智力和性格特征对有关艺术创作的新经验是开放的。当处于每月怀孕几率的顶峰时,女性更喜欢富有创造性的男性而不是富有一族。但米勒也承认,单是性选择这一个因素可能无法解释艺术的进化。他说:“艺术创作可能具有其它一些功能,用于展示性魅力这个功能是后来才具备的。” 艺术创作的其它功能到底是什么呢?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进化心理学家约翰·托比和莱达·科斯米德斯认为,寻求美感体验的想法促使我们了解世界的不同方面。出生时,我们的大脑并不具有这种功能。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布莱恩·伯伊德认为,艺术创作是展现智慧的一种方式,允许我们在安全环境下探索新领域。 另一种想法认为,艺术创作是适应社会的一种手段。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埃伦·迪桑纳亚克表示,一切艺术创作都是借助色彩和旋律创造一个事物或者事件,并通过迎合情感的方式使其具有特殊性。她认为,这一过程能够通过将群体团结在一起的方式提高我们祖先的生存机会。这种特殊性的获得最初是通过神秘或者超自然仪式,而后才让艺术品更富有美感。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我们的美感来自何处。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迈克尔·加扎尼加认为,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说,人类在发现确定图像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例如对称设计,或者说具有更强的审美能力,其中的原因不过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能够更快速地处理这些信息。 但他也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对一些艺术品给予肯定并不是因为它们让我们获得一种审美体验,而是因为欣赏或者拥有艺术品是地位的一种象征。米勒认为:“我们需要接受大量反直觉教育,才能区分当代艺术品的好与坏。而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获得较高的审美情趣。”
迷信 美国总统奥巴马喜欢在选举期间的早晨打篮球。高尔夫球手“老虎”泰格·伍兹(Tiger Woods)在周日的比赛中喜欢穿一件红色衬衫。即使从理性上说我们都清楚迷信没有任何作用,但是大部分人都存在迷信倾向。然而事实上迷信并非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布鲁斯·胡德(Bruce Hood)表示,通过大自然的巧妙设计,我们的大脑可以发现周围环境里的特殊结构和规律。我们还能根据因果关系得出结论,我们假设结果是由之前的事件造成的。这种将感觉模式和推断结合的产物,导致我们普遍存在迷信思想。胡德说:“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让我们进化出这些能力。”发现并对一些无法确定的因果关系做出反应,对生存至关重要。 如果我们的祖先认为草丛里发出的沙沙声是由风造成的,因为狮子出现的可能性非常小,那么他们可能很快就会被食肉动物消灭掉。为了及时获知这些关系,做出一些错误判断也是值得的。哈佛大学的凯文·福斯特(Kevin Foster)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汉娜·库克(Hanna Kokko)利用数学建模展示什么时候相信迷信比错过一个生死攸关的联系付出的代价更小。迷信思想一定受到进化的青睐。 宗教为迷信提供了另一个进化好处。邓巴(Dunbar)是“宗教适应时代发展”的观点的主要支持者,他说:“(宗教信仰)涉及到相信神灵世界和它的作用,即使这种虚幻世界并没有任何作用。”他认为宗教的主要作用就是劝说人们听从命令,从而增强凝聚力。宗教通过创作一个超自然人物,让我们相信它可以影响我们的命运,从而达到上述目的。 虽然迷信是我们的天性,但是文化和环境因素显然对个体的迷信程度具有很大影响。例如,当我们感觉自己无法控制命运时,就会变得更加迷信。一项研究发现,居住在特拉维夫等中东高危地区的人,比其他地区的人携带幸运符的可能性更高。另一项研究显示,每个经济周期的低迷期,美国福音教堂的增长率会迅速上升50%。谁都会受到迷信影响。胡德说:“我们会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改变自己的迷信倾向。”
接吻 接吻并不是所有文化中都有的一种现象,所以,那种体验嘴对嘴愉悦之感的冲动可能并不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尽管如此,你一定好奇为什么我们中间有这么多人“好这一口”,为何它让人感觉如此美妙。对于这个问题,科学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猜测。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对舒适、安全和爱意的初次体验来自同母乳喂养有关的嘴唇感觉。 除此之外,我们的祖先为了让孩子断奶,可能嘴对嘴喂他们嚼好的食物(今天,黑猩猩和我们中的一些人仍坚持这种做法),强化了分享口水和愉悦之间的联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接吻源于寻找食物。据说,成熟的红果实对我们的祖先吸引力**,他们还将这种吸引用于求偶,找到制作鲜红颜料的方法,将它们涂抹在生殖器和嘴唇上。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神经科学家拉玛昌德兰(V. S. Ramachandran)认为,由于红嘴唇在白种人身上最为常见,接吻或许始于北纬地区,随后作为一种文化在全世界传播。不过,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拉玛昌德兰本人也不敢确定这种说法,他承认接吻可能在人类历史上多次独立存在。 在涉及接吻的生理学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更为坚定一点。嘴唇是人体最敏感的部位之一,上面布满了同大脑愉悦中心有关的感觉神经元。研究表明,接吻可以降低应急激素皮质醇水平,增加催生素水平。 通过接吻,我们可以去评估与潜在伴侣的“生物兼容性”。近年来,有一个问题越来越明显,即那些与我们自身免疫系统最不相似的人的汗液气味对我们的吸引力**——我们与这些人有可能生出最健康的孩子。当然,脸贴脸的近距离接吻足以让我们闻到这种气味。 12万家医院招聘,60万名医生护士求职,上康强医疗人才网 www.kq36.com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康强药师网无关。康强药师网站对文中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